顾准女儿回忆郭永怀、李佩
作者:顾淑林
出处:《科学文化评论》第16卷第6期
与郭永怀先生的交往
1. 工作的由来
郭永怀的名字影响我的人生是1964年冬天的事。在那之前,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的系主任,我是这个系的一介普通学子,只能远距离仰望他。郭先生给力学系上课,我也没有机会聆听。郭先生还直接负责我们系的爆震物理专业,但该专业只收20名学生,清一色男生,我们女生就安静地学别的专业去了。
1964年末,我们五年级第一学期将要结束时,学校通知说1965年有少量的研究生名额,我和几个同学正商量是否报考,年级辅导员韩非平找到我说,你不要去报名考研究生,系里已经决定毕业以后你去力学所做郭永怀所长的助手。于是我没有报名,也没有太多的激动。由于家庭背景问题,我已受过不少折腾,所以对这个安排最终能不能成立,我并没有过高的期望。
不久我随高速化学反应动力学专业共50名学生的实习队,离开北京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做毕业论文。实习队在大连住的时间很长,寒假以前就出发了,在大连过的春节。我在卢佩章领导的研究室做大型制备级色谱柱气-固吸附分离规律的研究,这也是研究室任务的一部分。我们工作得很投入,早出晚归,几乎全部时间都在实验室度过,到现在大化所实验大楼灯火通明到深夜的景象还历历在目。
一直到7月上旬我们才结束工作回到北京。这时已经到了分配工作和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拿到的分配通知单是到中科院力学所报到,果然如韩辅导员告诉过的。在填写分配志愿的时候,我事实上并没有对以前的说法太认真,所有的志愿都选的是外地和边疆的单位。记得韩非平接过我的分配志愿书的时候,看了一眼我填的内容,微微笑了一下。8月底到力学所报到,力学所人事处张秀琴接待,说,你去郭永怀所长那里。
2. 从1965年年底到1968年与郭所长的交往
从1965年下半年到1968年底,我和郭永怀所长的直接接触极其有限。我们的谈话只有三次。第一次见面,他要我用一年的时间学习英语,安排我到科大研究生院上英语课,还要我通读朗道(lev landau)的理论物理学。我问他工作上需要我做什么,他说你读完这些再谈。他嘱咐我集中精力学习,问我能不能30岁以后再结婚,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能的。第二次谈话,我主动向他报告在大学学习量子力学的一些体会和疑问,这一次看来他很累,没有打算详细谈下去,只是说,我们会有时间讨论这些问题。第三次是在他的办公室外面遇到,他问我为什么没有坐在屋子里看书,我说我到11室去了,因为我同时是游雄领导的6405任务小组的成员,他说要坐下来,不要赶热闹。所有这几次谈话都是在我进力学所一年之内发生的。1966年6月 “文革” 开始,不久我被正式通知调到11室。作为郭永怀所长助手的安排事实上中止了。
间接的印象莫过于从力学所同事口中谈到的郭所长了。两个方面的口碑至今不忘。一是他治学严谨,对浮华不实的学风深恶痛绝,某人在与他谈工作时语焉不详,被他当面严厉斥责。二是政治上他实事求是不跟风。当时三年困难时期的经历记忆犹新,郭所长从来没有在 “大跃进” 期间发表事后经不起检验的跟风言语,在所里备受尊敬。
郭永怀、李佩夫妇
3. 1968年12月传来噩耗
1968年12月5日,一个不幸的消息使我们惊呆了。郭所长乘坐的飞机在北京机场上空失事,那是一架伊尔14小飞机,机上的郭所长和警卫员都遇难了。
晚上所里安排我和另外一位女同志去陪伴郭所长夫人李佩先生。他们的女儿在东北插队,一时还通知不到,只有李佩一个人在家。
我们到郭所长家里,和李佩先生在一起,大家几乎说不出一句话,屋子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后来我们留在他们家里过夜,我和李先生睡在同一间房间。整整一夜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翻腾母亲去世的惨状,又回忆起卢贤均出事那天和卢贤均夫人度过的一夜,这些都刚刚发生在那一年的早些时候。我一边默默地想,这个打击太大太突然,李先生可怎么挨过这一夜,一边准备着如果需要我为她做些什么,我可不能反应迟缓,一定要保证她绝对平安。就这样,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一直到早上。那一晚上李先生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极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李佩夫人!
据报道,郭所长的追悼会是1968年12月25日开的,但我对此已经印象不深了。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定格的一幕是开追悼会以前,我们到医院向郭永怀所长的遗体告别。在医院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郭所长躺在一张单人病床上,一幅大白被单把他的身体从头到脚盖起。从修长的体形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郭永怀所长,但是我们已经不可能见他最后一面。在被单的遮盖下,依稀可辨他那在烈火突然遭袭击中的身躯;在这最后的床榻上,他的手和脚都是蜷缩的,不能伸展开来。没有哭泣,没有言语,刻骨铭心的痛惜和敬意只有用沉默表达。
从此我彻底失去了在郭所长指导下学习和工作的可能性。郭所长离去以后我在力学所大院又工作了三年,为新建的七机部二院207所筹备车间;后来到离城70公里的房山,在燕山石油化学总公司研究院做石油化学工程师。1982年中国科学院招我回来加入新组建的政策研究室。1992年,我远走欧洲荷兰,在马斯特里赫特联合国大学的新技术研究所做高级研究员,2000年12月回到阔别9年的祖国。在1968年的时候真是怎么也想象不到,后来我竟然走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
4. 郭所长的教诲对我人生道路的影响
不论我走到哪里,在北京远郊的大山沟,抑或万里以外的异国他乡,郭所长的教诲与期待,以及耳濡目染中他的为人治学的榜样,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几位最优秀的人,得到过他们的关爱,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成了我人生的楷模,郭所长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位。
我所敬重的郭所长的期待和信任,在 “文化大革命” 的年月对我以至我的家庭曾经非常重要。1965年是我们家极为艰难的一年,9月初,我父亲顾准在中国社科院被第二次戴上 “右派” 帽子,是全国少有的 “二进宫”。我在第一时间即向力学所报告了这个变故,郭所长与我做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不会不知道。所以这个谈话和他对我工作的安排,对于处在无奈和凄苦之中的我的母亲和父亲,以及我的弟弟妹妹,显然也是一丝温暖与欣慰。记得到了 “文化大革命” 已经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已经在力学所车间劳动了,还间接地听说“郭所长有话,不要随便动顾淑林,我(指郭所长)有用”。现在想想,以后我曾不止一次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极端的痛苦迷茫之中,是这样的期待和这样的简单的话语,让我心中的火光不灭。它们不准我消极、沉沦!它们指点我:生命还有更高一层的意义,任何人没有权力在个人的困苦面前倒下。
在治学方面,我还想说两句。郭所长短短的一句“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我记了一辈子,时间越长越觉得有味道。在我的业务生涯中,到国外机构就职是遇到的挑战最为严峻的一次。那年我49岁,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我的同事都是外国名牌大学的博士。英国籍所长怀疑我究竟能不能胜任。我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除了完成日常的研究课题,最大限度地抓紧时间弥补基础理论的不足和提高英语能力,一年多以后我的英国藉所长惊异地问我,你怎么提高得这么快?我回答说,您一周工作多少天?一天工作多少小时?而我,一周工作六天半,一天工作14小时,秘密就在这里。同时我坚持像心中的楷模郭先生和我的父亲那样,任何时候都平实真诚地做事处人。在开始入所处于不利地位时,我做到放下架子承认不懂的就是不懂,后来即便在同事认可我的能力以后,也一样地 “坐得住,不赶热闹”,老老实实做学问。这来自郭先生榜样的力量,也来自我所不能忘怀的北京101中学的教养和我父母家庭的教养。
到了2000年上半年,我所在的联合国大学新技术研究所管理上出现一些问题,总部派代表到所里调查,根据群众反映,大学总部决定任命我在该所的管理危机期间担任执行所长,最终在2000年底我圆满完成了这一段使命,结束了我的服务。我很欣慰通过我的行为为中国学者在这个重要的国际机构赢得了信誉。这段经历清楚地表明郭所长的教诲给了我怎样宝贵的精神财富。
与李佩先生相处二三事
从1968年那个难忘的一夜以后,我与李佩先生在以后30余年中聚少离多,一直到我从西欧归国,那已经是2000年底以后的事了。此后一直到她辞世,我们来往比较频繁,她已经从我的导师的夫人变成我的导师。
30多年以后的李佩先生,头发全白,身体枯瘦,可见1968年与1996年(她独生女儿离世)的不幸带给她内心什么样的煎熬。在和李先生重新接触后,我感受到熟悉和亲切的是她更加理性的谈吐,对人更加的体贴入微和更加包容的宽广心态。
是李佩先生先找的我。大约在2005年,我接到李佩先生的电话,问:“为什么不和我们联系?”我被问住了。的确,回国以来除了家人我几乎没有和任何人联系。经过若干年的远离,再回到既思念又充满痛苦回忆的故国,我心理上有巨大的障碍需要克服,同时和原来单位也有一些难处理的问题。我说,是我不好,我在自我心理治疗,快要越过去了。我给李先生简单地讲了我的困境。
过了两天再次接到李佩老师的电话,告诉我她已经和中科院某位负责人谈了,还为我的事对有关单位提出了批评。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李佩老师平和的心态和关心他人的宽广胸怀让我感到羞愧。
不久以后我去她家看望李佩老师。时隔多年又来到老13号楼204单元。房间里的家具陈设依旧,他们的女儿郭芹已经去了。李佩老师依然淡定美丽,只是更加清瘦苍老。她已经从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主任的岗位上退休,过着忙碌的退而不休的生活。她关心中关村的社区建设,组织中关村老年活动中心的活动,关心老科学家们的家庭困难,“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从那以后我不时参加一点她在做的事,接触多了起来,对李佩老师开始有了更多的了解。
她为中科院离退休老科技干部定期组织报告会。李老师曾经要我帮她联系一个报告,题目是经济结构调整。我还直接做了自主创新的报告会,参加了学风问题的报告会,等等。从这些题目上看得出,李佩老师虽然年纪大了,但眼光依然尖锐,丝毫没有因为年迈而跟不上社会进步的脉搏。有一次我进到她的 “办公室” ——她家里郭先生原来的书房,看到桌子上、沙发上、地板上堆满了报纸和书籍,我窥见了她保持思想犀利的小秘密。李佩老师谦和地说,对不起,我来把沙发上的报纸挪开,又说,我保持阅读,才能不落伍。
大约在2009年,一次李佩老师及几位力学所的老朋友在我家小聚。闲谈中,我讲起我接触到的中科院研究生院的一项国际合作项目,说起我的批评意见。几天以后,李佩老师来电话,口气带着责备:“你说的事情我问了他们(研究生院的领导),他们说的和你不大一样,你去和他们谈吧!”我又小小地震惊。一来吃惊李佩老师那么认真:闲谈中提到的事她都一定要去反映,还顶撞了一句:“当时您也没有问清楚呀。”二来感到愧疚:和李先生对比,我的态度就消极多了。我立即与研究生院的领导约谈,带去了相关的文件,提出了几点建议,谈得很好。回来后把谈话的情况和带去的文件同样送交李佩老师一份,这次她很温和了。
我很认同2003年《科学时报》的一篇访谈,访谈引用了她的学生和同事对她的反映。和他们一样,在我眼里的李先生学兼中西,有很高的知性;对我们——犹如她在研究生院的工作中对待同事和学生——严格而从无疾言厉色,有尊严而绝无傲气。她从不长篇大论,任何时候都仔细倾听。她对自己做的许许多多的事看得很平淡,很少提起,谈话进退全都出于慈爱和责任。我问她,经过了那么多事,您怎么扛过来的?她的回答再简单不过:我没做什么;活着,就要做一点有益的事。
正是在2006—2010年前后,这位我从“郭所长夫人”开始接触的李佩,在我的心里升华再升华,从师母变成了老师。那是一个社会上弥漫着奢华附庸之风的年月,李先生没有钱,没有权,她说,“到中关村大讲堂讲课,我们没有钱,顶多一束花”(后来我知道那束花还是李先生从自己工资中掏的钱),可是我们愿意为她努力的事业做事,我们敬她,爱她,从为她工作和与她相处中汲取生命的能量。
我的这两位老师——郭所长和李佩老师,有着共同的气质,他们是老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典范。虽然他们的出身不同——郭所长来自山东的农村,李老师来自北京的世家,但他们都具有兼学中西的长处,融会了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营养,他们一样的宽阔而谦和,高洁而平实。他们同样地挚爱祖国和人民,科学救国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理想。郭所长当年为了回国不受阻挠当着美国同事的面烧毁手稿的事在力学所早已广为人知,多年以后李佩老师的一句话,“我们年轻的时候出国是为了回国”,也同样振聋发聩。
谈谈郭先生牺牲以后的李佩
在20世纪60—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政治运动中,李佩受尽折磨,前后被隔离审查达六年之久。在严济慈和郁文的关怀下,她于1976年调回北京,1978年出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主任,时年60岁。她的品格和学识一直要等到将近退休时才得到用武之地。
李佩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主持英语教学的十几年,是她工作生涯中最有声有色的时期,她的同事和学生能讲出许多感人的故事,可惜我不在场。我看到的李佩老师是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的年月,她的品格同样地在平淡中发光。
在我整理李佩先生的这一段经历时,常常感到痛彻心扉的惋惜。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极其浓厚的家国情怀,他们不论受到过多少整肃,一旦解除审查能够工作了,就拼命地干,李佩和其他许多人的经历都是例证。每当我回顾李佩先生的这段历史,心里都不由自主地说,对不起,李先生,让您受委屈了。我想,我们一定要从历史上的错误举措中吸取教训,那些举措伤害了我们事业的中流砥柱,耽误了许多人的大好年华!
1. 开创 “应用语言学”
1977年底,中国科学院决定全面启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的工作,请李佩筹备外语教研室并任教研室主任。
新建立的外语教研室只有三位教师,教英语的只有李佩一个,但研究生院第一年已经有800多名学生。于是李佩四处寻找英语教师,将一些在 “运动” 中受冲击离开大学的教授请到外语教研室来,她还四处奔走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待遇问题。
李佩通过各种渠道招聘了一些外籍英语教师。在与外籍教师玛丽(mary van de water)的交流中,李佩了解到了toefl和gre的考试情况,率先改进了国内英语教学方法。为了长久解决研究生院的师资问题,李佩创办了 “师资研究生班”(图2是李佩在研究生院上课)。由于李佩注重在科学知识与外语教学的结合之中来设置英语课的内容,国外的专家们称李佩开创了“应用语言学”。
说起考试现场,有一篇回忆文章这样描述:李佩走进考场,在黑板上写下 “honest”(诚实),随即转身走出教室,直到考试结束。请设想一下,这样的信任,这样的托付,考生们会作弊吗?有作弊的氛围吗?
2. 殚精竭虑服务社会
李佩离休后,过起了离而不休的生活。她依然站在研究生院英语教学的讲台上直到1999年,同时她办起了每周一次的 “中关村专家讲坛”。讲坛内容涵盖极广,不仅包括时事政治、科普、健康,还包括古代文学、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与法律。这些高质量的讲座吸引了很多离退休老人,也吸引了中关村的年轻人。
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 成立,李佩共组织了十多次全国性的科技翻译讨论会。会刊《中国科技翻译》于1988年创刊,荣获 “1990—1993年度fit最佳国家级翻译期刊奖”。
李佩还与郭慕孙院士的夫人等组织了 “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除了为退休学者举办医疗保健讲座,提供医疗咨询和义诊外,还成立了英语班、中老年电脑学习班、老年合唱团、老年手工制作、古琴学习班,举办各种展览。在她的带动下,中关村社区的离退休学者们有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她关心钱学森夫妇,关心钱伟长夫妇,关心郭慕孙夫人,关心任何一个在她周围甚至与她不期而遇的人。李佩说:“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注意健康,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尽可能为大家多做一点事。我没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点。”
李佩的晚年使人不能忘怀的另一个方面是她向社会捐赠了自己的一切所有,她捐出了郭永怀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出了家庭所有积蓄60万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此为基础分别设立了郭永怀奖学金。李佩逝世后的一次追思会上,郭传杰说起此事,2008年李佩与他联系要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捐款,郭传杰派了人去李佩家。后来他派去的人说他是哭着走出李佩家门的,因为那30万元中有些小票子,显然李佩把家中能够搜罗的钱票都放进去了。
其实,郭永怀李佩夫妇的社会公益捐助行动可以追溯到1965年。是年一月郭李夫妇把在国外的积蓄和回国以后认购的经济建设公债共约五万元人民币捐献给了国家。他们在给中科院领导的信中说:“这本是人们的财产,再回到人们手中也是理所应当的。” 力学所党委为郭李捐赠之事还特意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作了正式的报告说明。郭永怀获得的“两弹一星”金质奖章重一斤,她说捐就捐了——这使我想起了居里夫人把奖章给小孩玩的故事,这些伟大的人共同的特点是对金钱和物质财富普遍的轻视。
在我认识李佩先生的半个世纪中,我感受到她的境界在个人的经历和悲苦中升华。早年受到隔离审查,周末还要从合肥赶回北京照顾小女儿,常常拿个小凳子连夜坐火车奔波在合肥和北京之间,甚至一度有自杀的念头。然而,到她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我感到她换了个人,超凡脱俗,高大宽厚。她博大、睿智、深刻、谦虚,关心任何人而从不自大。我们,她身边的人,不时想念她,心向着她。后来想想又觉得有意思:她没钱,没权,可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她有一种吸引力呢?因为她有一种渗透人心扉的能量,我们不时地需要靠近她来充实自己。郁百杨(郁百杨是位导演,《爱在天际》的作者,较晚才认识李先生)说过一件事,他曾经送过一条围巾给李先生,之后每次郁百杨去看望李先生,总看到李先生围着那条围巾。这不是因为那条围巾有多么金贵,而恰恰是李先生通过细枝末节表达出来对人的尊敬与关心。
那么,推动李先生在高龄之下不断升华的力量来自哪里?我的体会,一是来自家国情怀。李先生和郭先生一生不敢懈怠,期盼用自己的力量多多少少实现一点点 “齐家,治国” 的大目标。我在别处还补充说过,郭先生和李先生的品德除了 “家国情怀”,还应该加上 “人文关怀”。他们爱人,亲近人,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情怀。
这也使我联想起马克思在17岁时写下的中学毕业论文中表达的:“如果一个人只是为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推动李先生在高龄之下不断升华的第二个动力来自爱的力量。她说过,“爱一个人,就要像他一样”。我们看到,李先生爱郭永怀爱得刻骨铭心,在郭先生离开我们以后达半个世纪之久,她一直在铭记、守望、追随郭先生的事业和品德。李先生在爱的力量之下,完完全全换了一个人。
李佩观看《爱在天际》音乐剧时有一件轶事:剧情中有一句台词,扮演李佩的演员对扮演郭永怀的演员说,“你不回来我不老”,此时全场默然良久。当我听到这件轶事,禁不住眼含泪花。
2016年在山东荣成市,青岛电视台找我谈郭永怀和李佩先生。访谈的最后,主持人问: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郭先生、李先生的一生?我回答:“伟大寓于平凡!!” 的确,这就是从郭先生和李先生的榜样中我所感悟到的人生的终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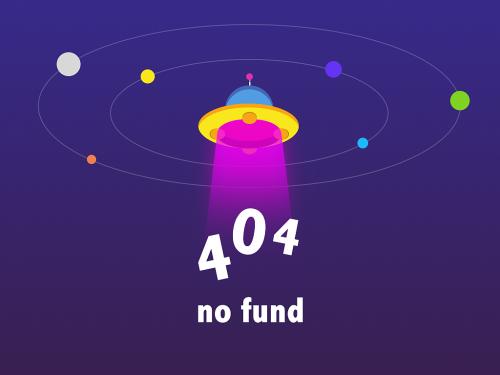
诵读人:生态环境中心 离退休第一党支部书记 张康生